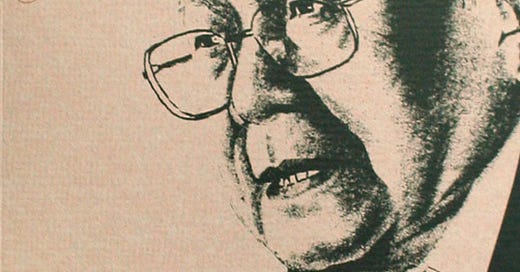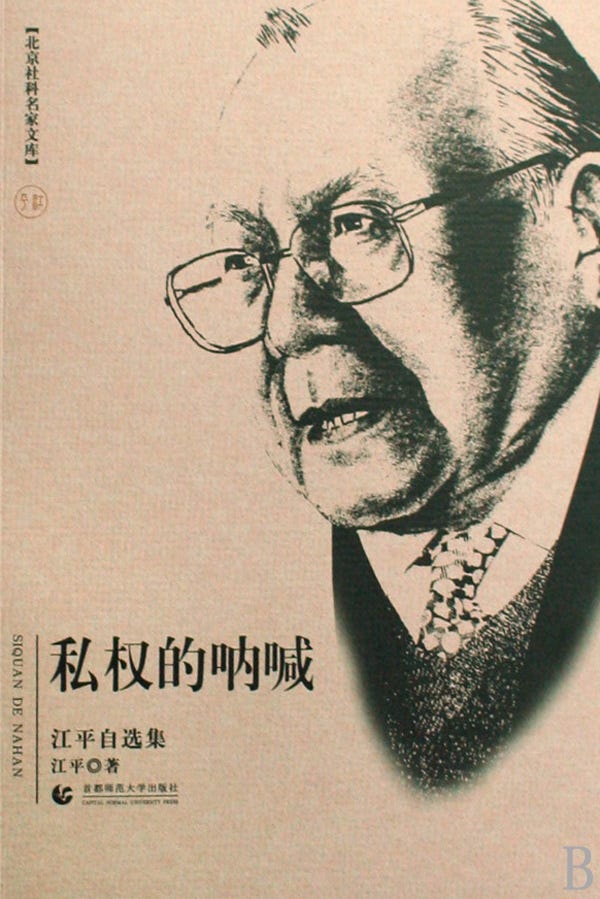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平先生千古!
大概是2016年某一天,耶鲁大学中国法中心主任葛维宝教授访问北大期间,特地要我代他向一位“巨人”(giant)转达问候。他说了不止一次:“他是一位如此高大的巨人!”
江老师个头不算大,但他就是那位“巨人”。江老师去世,悼念的声浪经久不息。对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影响的赞美铺天盖地,已无需多说。这种现象似乎只有在国家主要领导人去世时才会出现,所不同的是,这次人们的赞美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毋庸置疑,江老师获得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人士的一致高度评价。这在当代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我想体制内的人尊敬他,不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全国人大立法部门担任领导,主持过重大法律的起草工作,而且也因为他们确实敬佩江老师的高大人格。虽然他们自己达不到他的高度,但也不免被他的人格感召力所感染。
广义的“体制外”(不在体制内担任领导职务)人士尊敬他,首先因为他是“法大永远的校长”。他在三十四年前那个夏天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了一切。即便之后什么都不做,也足以让他进入“中国最伟大的校长”之列。他显然不只是法大的校长,而是为这个国家所有大学的校长树立了一个坚守道义底线的楷模。“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江前校长以行动实践了这条儒家底线原则。在以往,这也许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但近几十年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校长能像他这样做到这一点。
我天性闭塞,很晚才认识江老师。大约2005年的一天,我去参加一个法学研讨会。到得晚了,坐在后排听江老师演讲。中气十足的演讲完毕,江老师意犹未尽地走下讲台。我匆忙和他打了个招呼,简单寒暄了几句。他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好几,但走路的姿态可以用“风风火火”来形容,有一股所向披靡、万夫不当的气势,完全看不出一个老人的样子,更不用说还装着假肢呢——即便在前几个月为他祝寿的午宴上,我都没想起他的一条腿不方便;即便他去世之后,和他很近的学生们还在争论义肢是装在左腿还是右腿上!他从来是这么一位精神饱满而又风度优雅的儒者。
初识江老师,能感觉到他自然流露着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坐在那里,身上更有一股“温而厉”、“不怒而威”的夫子之风。有一幅油画把他画得比较威严,但我倒不认为它全面体现了江老师的个性。一旦接近他,便很快发现他其实是很随和的,而且极具包容心、同情心。甚至偶尔会看到对江老师的个别非议,大意是他终究是一个“体制内”的人,对体制过于“温柔”,没有充分用自己的影响力对一些倒行逆施大声疾呼——尽管他不止一本书的书名就有“呐喊”二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这没法强人所难,江老师就不是一个动辄声色俱厉的人。他温和的一面使这个体制没有把他定位于“对立面”,但实际上他自己也一直被死死“盯着”,以至于哪怕为他组织一次生日聚会都越来越难。
我知道江老师特别忙,平时不忍叨扰他。但偶尔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叨扰的时候还是一定会叨扰的,而每一次江老师都义无反顾地给予宝贵支援。2016年,维权人士郭飞雄因抗议不公待遇,在狱中长时间绝食,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因为这件事已造成很大的国际影响,当时双方都有点下不了台。解铃还须系铃人,走出困局的关键在于监狱管理部门改变做法。我带着声援信,和另一位法律人登门拜访江老师,解释了体制内学者支持民间力量的必要性。江老师二话没说,立即同意联名支持。加上其他几位老先生和中年学者加持,这封信很快就发挥了作用。这只是江老师作为体制内学者为民间呐喊的一个例子。
江老师的逝去使得中国体制内外断了一根关键的纽带。集体制内外的荣誉于一身,他曾让中国看到改良的希望。近年来,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了。疫情前有一次聚会的时候,面对每况愈下的法治状况,他自己有点黯然地说:我们这代人是看不到这一天了。我相信,江老师这么说的时候,心里一定是不服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像他这样的改革资源今后只会越来越稀缺。对于改良最重要的是,体制内需要有人像他这样心怀体制外的事;这样,体制外的人才能在不满的同时基本认可这个体制——至少体制内的某些人,至少对这个体制心存希望,内外产生的合力共同推动体制向前走。如果随着江老师这样有风骨、有底线的一代“君子”慢慢逝去,这2个体制尽剩下一群只会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小人”,中国的法治改革何以为继呢?
当然,我不想以悲观的基调结束这篇追忆,这样无疑会辜负江老师对法律人的期待。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江老师那代人已经为改革开放年代亟需的立法、法治以及法治教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其实假如当年按照他那代人的相对沉稳与保守的改革思路走下来,中国法治之路本来会更平顺一些。但历史没有假设,不论是否期待,“谁来推动法治”这个问题早已摆在我们面前,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超越了法治的范围。英年早逝的法大教授蔡定剑说过一句名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看来,历史还得再给一次机会;中国法治要向前走,我们还得把当年没走对的路走对了。
我相信,中国法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必然是艰难曲折的,持之以恒地走下去需要江老师的大智大勇。他是每一个中国法律人的榜样。我们需要像他这样,不曲学阿世、不媚上欺下、不愤世嫉俗、不怨天尤人,立天下正位,行法治大道,守道义底线,“只向真理低头。”我也相信,江老师对中国法治和法律人是有信心的。他的精神将永远伴随我们,激励后学前行。
2011年5月23日,北大法学院凯原楼开张不久,即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那天晚上,江老师作为燕大校友做了题为“中国法治的困境与突破”的讲座,梁治平、贺卫方评论。讲座自然座无虚席,精彩纷呈。我把讲座结束后学生提问的最后一个专门给江老师的问题和他的解答留给大家,以此和大家共勉:
学生:江老师,你的中国梦是“法治天下”。我正是看到您的榜样,才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但现在法律人陷入一种困境,法律和利益越来越挂钩,很多法律人的初衷好像不再纯粹了,律师有陷入刑事追责的陷阱等。总之,法治梦很可能丢失。您觉得年轻一代的法律人要如何继承您的中国梦?该怎么做?
江老师:我很无奈,无奈的情况下就是多呐喊一点吧。我最近两本书都带有呐喊的意思,一个是《我做的只能是呐喊》,还有一个我自己整理的学术论文集,叫《私法的呐喊》。我觉得法律人的初衷已经不能够很纯粹。这个应该这么说,因为法律并不是抽象的东西,法律既是谋生的工具,也是治国的工具。你谋生还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够为了谋生而忽视了法治的理念,这个是最重要的。有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但以逃避法律、规避法律为目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律师如果走到这一步尤其可怕。所以我是特别劝在座的诸位,不要忘了法律和医学是最古老的两门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但是这两个科学都要求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必须特别高。因为最精通医术的医生有可能成为一个最会杀人的罪犯,因为他最懂得想法子杀死一个人而不被察觉。法律也是这样。如果用法律亵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注意法律人的道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