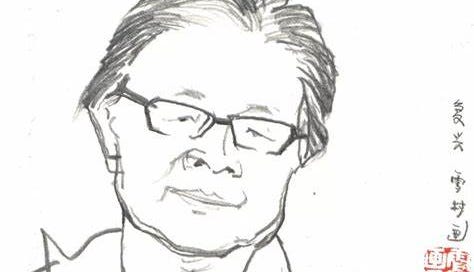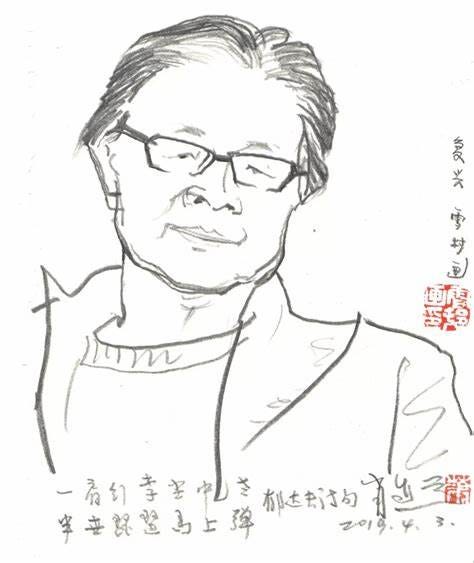肖复兴|书边草(续)
肖复兴,北京人,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壹
重读沈从文的《边城》,书前有他1934年写的一则题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至于文艺爱好者呢,或是大学生,或是中学生,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同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
整整九十年过去了,文坛的这种习气,似乎依然如故。沈从文说的“文坛消息家”一词,却很新鲜,如今似乎没有这个词,或者说不用这个词了。但是,“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都还健在,这几个词,延续至今,依然在用。
沈从文所说的能够控制、支配文坛的这种习气,九十年过去,似乎没有什么花样翻新的太大变化,依旧是这些能够控制、支配文坛的这些大佬,和聪明出版家联手,“为国内新出版的文学书籍”站台。不过,如同老酒古法酿造,自有古法的道理,尤其如今新书出版数量泛滥,鱼龙混杂,想让自认为的好书不被淹没,请这些人友情出演,吆喝几声,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
问题是,形成了经年不变的这种习气中,有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近年来,新书发布会、研讨会越来越成上升趋势,多如牛毛,其中孰好孰劣,哪本书真好,哪本书真不怎么样,已经如真假王麻子刀剪一样,让读者乱花迷眼,莫衷一是。
有意思的是,在文坛新书出版这样的供需关系中,聪明出版家或许因出版社不同,需要经常变脸,但理论家和批评家却是很少变化的。如果有心人将某一品种的新书发布会、研讨会,这一年出席的名单列出来,会看到总是那老几位。这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姜是老的辣。
问题是,谁是沈从文说的那种“文坛消息家”?自然,如今,沈从文讥讽的“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并不多见。但是,拿着一本书,对着镜头,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过年话,一本正经的空洞话,甚至拔苗助长的捧场话,却是屡见不鲜。无疑,这些便都是聪明出版家请来的“文坛消息家”。至于为什么要不惜重金请来“文坛消息家”,大概也不仅是为了卖书,更不仅仅是为了“很诚实天真”的读者——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了。
当然,如今,更有视频带货的主播,以及网络上雇来鼓吹的枪手,这样的新一代的“文坛消息家”,大概沈从文未曾见过,想都没想过。
贰
孙犁晚年曾说:“我就爱读‘繁复’的史书。”
1988年,他写过一篇《读〈旧唐书〉记》共十节的长文,其中第三节《郭子仪》,写自己以前读《资治通鉴》时,牢记于心的郭子仪三件事;读《旧唐书》,这三件事全部得到验证,言其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亦即《旧唐书》写得不错。
这三件事中,第一件最有意思。写郭子仪和日后官居相位的卢杞之间的关系:“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从,并从不避讳。‘及闻杞至,子仪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子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
《读〈旧唐书〉记》第四节,即写到读《旧唐书》中的“卢杞传”,传中写卢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下面写他“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果然是“形陋而心险”。果然是得罪了他“吾族无类矣”。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三件小事,其它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回答这个问题时,孙犁说:“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个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这便牵扯到文章的作法了。如今,不少报告文学,或所谓的非虚构文学,所写的大多也倒不是帝王本纪,却不少是帝王本纪史诗的写法,和粉碎“四人帮”时报告文学的时事性、批判性和文学性,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篇章中,看到所写的大小人物,多不是这样的些微小事,而多是谋略争战,攻城略地,成为一本本大小功业账簿的陈列。遗憾的是,孙犁先生曾经叹曰“那就太没意思了”的某些宏伟篇章,如今的作者、论者,甚至孙犁先生曾经说过的被有些人唬住的“书盲”类读者,并没有觉得“太没意思了”,反倒觉得“有意思”,甚至赞曰“太有意思了”。
叁
如今,解说古诗,流行为一门显学。尤其对唐宋两代的杜甫与苏轼的解读,连篇累牍,旁征博引,杂说纷纭,厚厚大书,不止一本。
重读冯至的《杜甫传》。虽是1962年旧作,已过去了62年,却依然觉得是言说杜甫最好、最简捷,也最让人信服之作。
《杜甫传》共有十三节,第十节《再度流亡》中,写了这样一段在四川梓州杜甫和章彝的交往。章彝时任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也就是说,章彝是掌管此一方的长官,杜甫是沦落此地的流亡诗人。在如此地位不对等的人物关系中,书写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是小说和戏剧的写法,却不作材料的铺陈,没有学问的卖弄,避去煽情的演绎。区区几百字,立论明晰,写得干净利落,如刀削斧凿的雕刻,将这段流亡中杜甫的形象和心理、心情,凸显得可触可摸。
冯至写道:“杜甫在这时期内,衣食无着,生计完全依靠那些‘边头公卿’。这些使君、县令只知道杜甫能诗能文,懂得一些药理,用到他时,便‘肥肉大酒’相邀,酒肉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友谊。梓州为东川节度使所治,自从成都事变后,地位更为重要,无论进京还是入蜀,都成为官吏们往来的要道。那些地方官常常设宴迎送,杜甫也陪居末座,写了许多陪宴和送别的诗,这些诗多半是应酬的作品,粗浅无味,与前面提到的那些政治诗又成为一个对照。这正是他的最伤心处。他又和在长安时一样,自称‘贱子’,诗题中‘陪’字也一再出现了。”
只有两百余字,却将地理(梓州要为道)、历史(过去在长安)、当时的背景(成都事变后)、杜甫的现状、当地官员的需求,以及杜甫“最伤心”的心理和心情,一一勾勒出来。简笔,却是信笔,关键是没有过度的解读,留白给读者。
这一切只是老戏里主角出场后的开场白,接着,才引出另一个主角章彝的出场,冯至写杜甫“得助最多而最须小心侍奉的是章彝”。“杜甫不得不陪他宴会,陪他迎送客人,陪他游山寺,陪他打猎……”,一组蒙太奇在脑海浮现。最后,他引杜甫的这几句诗总结性地做旁白:“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写得真是深痛沉郁。既看出杜甫痛彻心扉的无奈和真诚的自剖,也看出冯至先生笔端的凝练,把对杜甫的理解藏于纸后。
62年过后,重读此书,多有象外之意。“失身为杯酒”者常有,却未见得谁“自觉成老丑”。
肆
于非闇先生的《书画过眼》,专谈书画,是本老古董,冠以新书名,内文均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写。于先生是有名的画家,又出身世家,与时贤尤其书画家过从甚密,自然见多识广,方可笔落缤纷。
书中有一篇《雪厂上人》。雪厂,是释瑞光,号雪厂,民国期间,非常有名。他是北京城南烂漫胡同莲花寺里的住持。清末民初,莲花寺非常出名,军阀混战,战火连天之际,陈石遗、姚茫父等人曾在莲花寺中寓居避难。姚茫父一住竟住了长长的二十年,自称为“莲花庵主”。后来,莲花寺更是名流常集,不仅京城画家,就连京剧界的名角如梅兰芳、王瑶卿、程砚秋等人,也常踏破小小寺庙的门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寺中有雪厂主持。当时《顺天时报丛谈》说:“(雪厂)工绘画,喜风雅,一般名流多雅集于此。”
雪厂确实画技不凡。于先生称他:“其画笔,今世之苦瓜和尚也,见其画益奇之……豪放肆恣,俨然大涤子。”这里说的苦瓜和尚和大涤子,指的是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将雪厂比之石涛,很是了得。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画技了得又团结那么多画家文人艺术家的和尚,却最后穷困潦倒,只活了54岁。于先生在书中说:“(雪厂)不幸而遁入空门,于寂静清空讽诵礼忏之余,独不走门第,传布施,而其人役役于苦瓜,垂三十余年,南北知名,而独以穷死。”
可见这位和尚,不是花和尚、俗和尚,宁守清贫,独以穷死,不失操守,更不是总想攀附皇上的石涛这个苦瓜和尚所能比之。如今的画家(包括遁入空门又还俗者),哪一位能赶得上当年的雪厂?倒有不少早已暴富,左拥娇妇,右攀权势,不可一世。“气节陵夷谁独立,文章衰坏正横流”,大师遍地,雪厂何在?
伍
重读《静静的顿河》,是第四本,最后一部。这是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人的译本。买这套书时,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每本不到两元钱,四本不到八元。
读到后面,有一段格里高利和儿子米沙关于战争争论的描写。肖洛霍夫写道:“(格里高利)不喜欢跟孩子谈论战争,但是米沙却觉得战争是世界上最有兴趣的事情。他时常用各种问题纠缠父亲,如怎样打仗啦,红军是什么样的人啦,用什么打死红军啦,以及为什么打死他们等等。”
这些简单天真的问题,格里高利回答不上来。但是,米沙却步步紧逼,一直问道:“好爸爸,你在打仗时杀过人吗?杀人的时候害怕吗?杀死他们的时候流血吗?流很多血吗?比杀鸡的时候或者杀羊的时候流的血多吗?……”
这一连串如机枪扫射的问话,格里高利如何回答?他只是恼羞成怒又无奈地冲着米沙高喊:“不许再谈这个!”
格里高利的母亲也冲着米沙喊:“又生了一个刽子手!上帝宽恕,宝贝儿,你为什么心里总想谈这个可恶的打仗的事儿呢?”
米沙的回答,让格里高利和母亲都没有料到,更让我听了胆颤心寒。
米沙说:“不久以前我看见爷爷宰了一只羊,我并不害怕……可能有一丁点儿害怕,可是不要紧了!”
米沙每次谈到战争的时候,格里高利就感到心里的惭愧。他不想让儿子想到战争,但是战争每天每天都要人想到它。每天每天啊!这就是格里高利父子两代人存在时触目惊心的现实,他们的生活里、脑子里、心里,弥漫着的都是炮火硝烟。
这一段只有一页半的描写,我觉得是全书最精彩的书写之一。因为我想起了眼前的战争,乌克兰的土地上战火蔓延了两年半之多,“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当年,格里高利也曾经驰马挥刀,将战火魔魇般燃烧到那里。战争,将格里高利的心灵扭曲,将他的生活变形,将他的爱情葬送,令他家破人亡,使他的命运走向彻底的崩溃。当然,这里有战争发生的时代背景的介入,有哥萨克民族性格的因素作用,也有格里高利自身的思想局限和行为所致。但是,诸多因素中,战争,无疑是首要的。如果没有战争,格里高利会怎么样?他的儿子米沙又会怎么样?还会顽固地问父亲这样的问题吗?
这一段,我反复读了几遍,每次读,都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战争的阴影,竟然深刻影响并塑造了一个小小孩子的身心:从害怕——到不要紧了——到最有兴趣,战争对于一个孩子心理与成长历程潜在的渗透、衍化和遗传,是多么的可怕!
读这部小说的同时,我也看了三集气势恢弘的电影《静静的顿河》,听了李野墨一百二十回深沉苍郁的广播《静静的顿河》。可惜,都把这段删掉了。
陆
三伏暑天,热汗蒸腾,读钱仲联校注的《剑南诗稿》第四卷,其中一首七律,有这样几句诗,写宋时夏日情景:“风生团扇清无暑,衣覆熏笼润有香。竹屋茆檐得奇趣,不须殿阁咏微凉。”从唐宋到现在,上千年来,炎热天气,依然需要风凉解暑,只不过,如今的空调,取代了扇子而已。
此诗下面,有钱仲联先生的一则注释,注释比诗更有意思,方才是放翁所得的“奇趣”。注释引《广卓异记》所记载一则唐朝皇帝的轶事,也关于夏日风凉:“唐文宗夏日与诸学士联句:‘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曰:‘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文宗独讽公权两句,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
《广卓异记》,是宋代一位叫乐史的人编撰的一本笔记。这则轶事,虽简单,却将唐文宗和柳公权两人写得惟妙惟肖,有言有行亦有诗,还有题写于殿堂墙壁上的书法淋漓,多维立体,环绕回声,很是生动。唐文宗这个皇帝,和宋徽宗爱作画一样,钟情作诗,尤爱五言。唐文宗当政时,柳公权官居侍书,已经侍奉了文宗前两代皇帝穆宗和敬宗,三朝元老,长居朝中,前倨后恭于皇帝身前身后,自然懂得眉眼高低,将皇帝的心思揣摩得透彻。皇帝前嘴刚说出上联,他立刻就对出下联。对于一个诗人,这样的文字游戏,当不在话下,关键是要对出皇帝的心思,即皇帝身上痒痒了,你要立刻递上一个玉制的痒痒挠。
看,皇帝说了:“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
柳公权立刻接上:“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
皇帝吃凉不管酸,大热天的,众人叫苦连天说太热了。他偏说:我就爱夏日,还希望它再长点儿才好呢!整个一个不食肉糜的主儿。
柳公权的厉害在于,他明明知道,宫内和民间自然大不一样,再热再长的夏日,宫内自有宫女的宫扇不停在摇,还要冰块散凉驱暑。他却要拍拍皇帝的马屁,说是熏风自来,殿阁生凉。于是,皇帝高兴了,立刻夸他“辞清意足,不可多得”;而且,立刻让他“题于殿壁”,发挥他作为书法家的特长。唐诗多了,辞清意足的多了,未见这句就是不可多得。
皇帝高兴了,就是不可多得。皇帝为什么高兴了?因为柳公权适时适地地递上了痒痒挠。我们就可以知道,柳公权这个官就是这样当的,而且,就是这样当得如此长久。仅仅会作诗和书法,是远远不够的。
读放翁诗,对柳公权如此之诗与言行,放翁显然是不屑的。解暑的风凉,他只须在竹屋茆檐下,一把扇子就够了。
同样是暑天风凉,皇帝、柳公权和放翁的态度,是这样的大相径庭。来自宫廷殿阁,来自竹屋茆檐,是这样的泾渭分明。夏日天热,是客观,属于自然,即是由老天爷在管着,谁也奈何不得。但风凉却不尽归天管,人亦能为。居庙堂之高,自有宫女和差人等人工制风;处江湖之远,如放翁手摇一把扇子即可。
当然,风凉的大小、清爽和质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谓夏虫不可语之冰。可见,天热可以一视同仁;风凉却从来难以那么平等。“不须殿阁咏微凉”,你可以随便咏你的微凉,“不须”,只是你自己的“以为”;“殿阁咏微凉”的柳公权,却是官当得如唐文宗所言夏日一般长,死后获赠“太子太师”称号,了得!放翁却是忧愤成疾,死于山阴乡中,虽有《剑南诗稿》多卷,却未有一首诗荣幸题于殿壁,更是终未获得皇帝赐予的一枚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