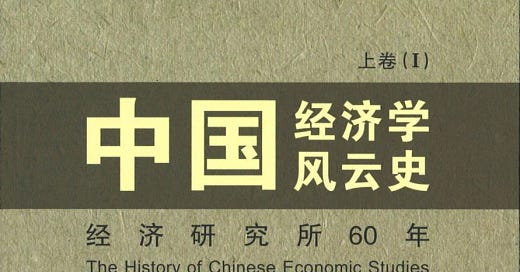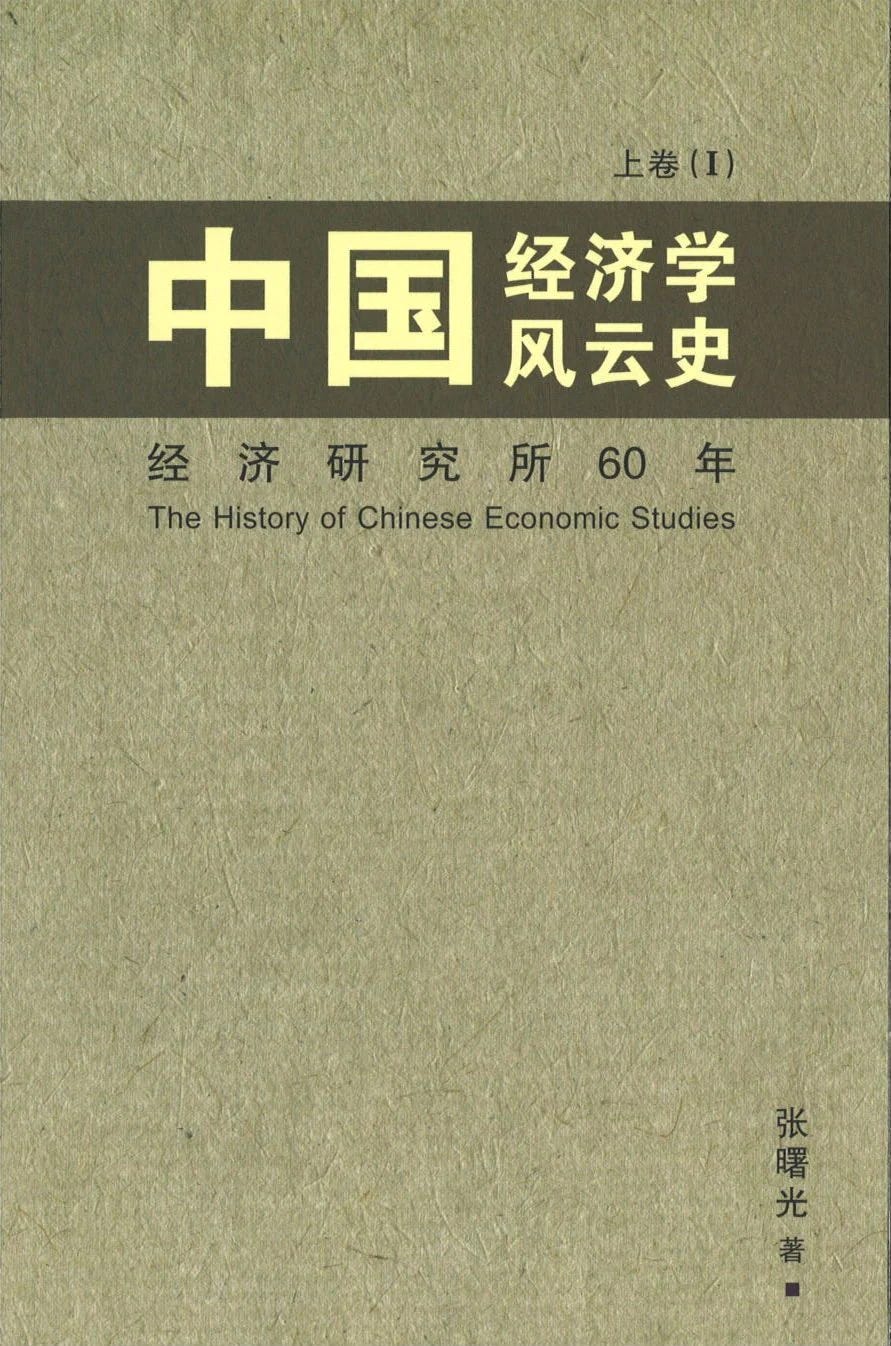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一
从2009-2016年,笔者做了一项思想史研究,撰写了《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经济研究所60年》(两卷四册,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6、2017、2018)。上卷记述了围绕着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下卷评介了顾准、孙冶方、董辅礽、刘国光、吴敬琏等15位经济所重要学者的生平活动和学术思想,从一个方面再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为此,笔者访谈了200多位有关人士,阅读了500多部著作和大量论文文献,其中有不少传记,比如,《毛泽东传》、《张闻天传》、《顾准传》(2种)、《孙冶方传》、《董辅礽传》(2种)、《刘国光传》、《吴敬琏传》(3种)、《张卓元评传》以及《胡乔木――中共中央第一枝笔》、《薛暮桥回忆录》等,颇有一些感触。
传记主要是指正式传记,还包括个人的自传、自述、回忆录之类。其性质是一种人生的回望和书写,其作用在于昭示后人和来者,学习和享受人生。正如美国爱默生学院教授默里•施瓦茨所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传记总是一种个人、文化和制度性资源的耦合。传记既是一种人生书写,也是一种人生解读,一种被讲述和解释的人生”。
传记与文学和历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传记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
从形式和写法上来看,传记类似于文学。除了不能夸张、虚构以外,它可以使用叙述、抒情、议论等多种表达方式,形象地再现传主的生平和经历,生动地塑造传主的典型形象,深刻地刻画传主的人物性格,给人以文学艺术上的美感和享受。
从内容和实质上来看,传记就是历史或近于历史。传记不是“传奇”,更不是“戏说”,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不能夸张,不能虚构,不能捕风捉影,不能子虚乌有地编造。至于评价,作者有自己的立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做出不同的评价,但必须恰如其分。过犹不及,均不可取。
中国有着传记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不论本记,还是列传,既是传记,也是历史。是用文学形式书写的历史。
除了自传、自述、回忆录以外,一般说来,正式传记有两个主体:一个是传主,一个是传记作者。两个主体的角色和作用不同。
传主是传记描写和记述的对象。一般都是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要人物,他们或者制造和主导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或者是参与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或者是有重要的发明创造,或者为他人的福祉和人类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或者为人类制造了严重灾难,因而有值得记述和书写的东西。不过,传主也有不同类型,其写作也有不同要求。为艺术家、作家作传,可以有描述性细节,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的传记,必须慎用细节描述。
作为传主,有在世的,也有逝世的。以前,为在世者作传的比较少,现在逐渐流行起来。在世的,作者除搜集有关资料外,还可以与传主直接交流,借以把握传主的精神气质和处事风格。去世的,作者只能根据遗著、遗物和他人的回忆去思考和书写,借以揣摸传主的心里,与传主进行精神上的交流。
在传记中,传主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传记作者则处于主动的地位,如何记述和描写要由作者做主,传主最好不要参与,更不可强加于人,审定修改。否则,就分不清是自传还是传记。为此,作者就要熟悉传主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认真阅读传主的著作或遗著,以及他人的回忆和评论,尽可能把握传主生活和活动的第一手资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独立自主地思考和书写。如果作者不作调查研究,不阅读和掌握传主的基本材料,仅凭对传主的访谈就去写作,无异于传主假作者之手,为自己树碑立传。如果传主与作者联手,有意歪曲和掩盖历史,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那就是欺世盗名,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传记作者是各种各样的人,其创作目的和创作态度也不相同。创作目的不外乎兴趣和功利。没有功利的兴趣最好,这样才能采取平视的创作态度,但能够这样做的寥寥无几,现实往往不是兴趣超过功利,而是功利超过兴趣,甚至就是一种交易,因此,难免发生扭曲。创作态度通常有三种:即平视、仰视和俯视。平视就是与传主平等相待,在精神上保持人格独立和自由意志,不卑不亢和独立自主地观察和再现传主的一生。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和选择。选择这样的态度和作法,就不会为表象所迷惑,也不会为传主所左右。而仰视和俯视都不可取。因为不论是仰视,还是俯视,在人格上作者与传主都不平等,都有高下尊卑之别。这就无法保证传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然而,在当前国内的传记写作实践中,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仰视,特别是为名人作传。作者往往为传主的光辉形象和高大人格所镇摄,为尊者讳,从崇敬而胆怯,变尊重为谟拜,不敢触及传主的缺点、局限和失误,甚至把缺点和错误写成优点和成绩。于是,很多名人传记不是高大全的形象,就是伟光正的角色。然而,过分的拔高和颂扬反而使传主的形象受损,变成高不可及、苍白无力、悬在半空中的人物。其实,不论是领袖统帅、英雄模范、名人大腕、贤人智者,都是常人,都有人性的弱点和缺失,不可能完美无缺、一贯正确。正所谓“金无赤足,人无完人”。
在传记写作以及传主与传记作者的关系中,《史蒂夫·乔布斯传》及其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Isaacson)可以成为一个榜样。艾萨克森是原《时代周刊》主编、CNN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撰写过爱因斯坦传记、基辛格传记、富兰克林传记等。《史蒂夫·乔布斯传》是乔布斯唯一授权的官方传记,是艾萨克森在乔布斯去逝前两年中与传主面对面交流40多次、对乔布斯100多位家庭成员、朋友、竞争对手和同事的采访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史蒂夫·乔布斯传》的珍贵之处在于,在乔布斯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除了医生、家人外,作者艾萨克森是乔布斯少数见到的几个人之一。最后一次采访结束时,艾萨克森曾忍住内心的悲伤问乔布斯,他二十年来拒绝媒体、刻意注重隐私,为何在过去的两年里,为了这本书,对自己如此开放。乔布斯回答说:“我想让我的孩子们了解我,我并不总跟他们在一起,我想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也理解我做过的事”。 乔布斯罕见的真情流露,对这本书的撰写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乔布斯承诺对艾萨克森不干涉其传记内容,鼓励他说实话。艾萨克森撰写的近600页文字也为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乔布斯 。
二
从上一节的讨论可以看出,传记既然是书写和回望人生,其基点是真实,不能有意拔高或肆意贬损,不能以偏概全和隐恶扬善,更不能蓄意编造。要使人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生。文学的手法可以运用,叙述、形容、比喻、刻画、评论都可以,但不能夸大,不能虚构,不能无中生有。
然而,现在的很多名人传记不是这样。传记作者不仅采取了仰视的态度,而且随意虚构,蓄意编造,一个个都是高大全、伟光正的角色和形象,把传记变成传奇,甚至戏说。
下面,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几个名人的传记作为案例,加以分析和讨论。
案例1:《食堂报告》的真相与《孙冶方传》的记述
1959年5月10日,孙冶方派到河北昌黎的经济所工作组完成了第二个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人称《食堂报告》。由组长董谦带回经济所,在所领导小组会议上进行讨论,孙冶方参加了会议,并且支持和赞同报告的观点。据说会上没有原则性不同意见,由董谦按照组织程序上报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河北省委、昌黎县委;5月23日刊登在中宣部内部刊物《宣教动态》第36期上,题目改为《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并使用原文中的话修改了七个分节小标题:将“食堂与妇女劳动力解放”改为“食堂化并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将“食堂与粮食问题”改为“浪费粮食”;将“食堂与肥料”改为“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将“食堂与燃料”改为“燃料紧张”;将“食堂的房屋设备”改为“占用房屋增加社员负担”;将“食堂与生活集体化”改为“只有大集体,得不到小自由”;将“食堂与管理水平”改为“缺乏管理食堂经验”;原稿关于改进食堂的建议部分没有小标题,编者加了“认为解散食堂,化整为零,可以解决许多矛盾”的标题。
毛泽东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了这个报告,并把它作为庐山会议上的一颗重磅炸弹,于7月23日批判彭德怀时扔了出来。毛泽东说,公共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不点名地逐条批判《食堂报告》,将其与帝国主义反动派放在一起。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方面批判反对公共食堂的人,一方面大力推行和发展公共食堂,加剧了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直到1961年中,才在“大兴调查研究”的名义下,不得不解散食堂。
在反右倾运动中,经济所党总支一方面把董谦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斗争,另一方面把《食堂报告》作为《反右倾学习参考材料之一》,加了如下的“编者按”印刷全所:“这份材料是昌黎工作组的一部分同志参加写出的,没有征求过核心小组的意见。现在发给大家供讨论农村食堂问题的参考”。对于经济所党总支这种推卸责任的编造,孙冶方从未提出异议,加以纠正。因此,直到临终,董谦对孙冶方始终不能原谅(关于公共食堂和“食堂报告”的详细史实,请参见《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第005章)。
然而,邓加荣在《孙冶方传》中写道,孙冶方“收到报告不单感到满心欢喜,而且满心感谢,立即在报告上签署意见,直接地向中央呈报上去。事情之发,也许正像古人说的,‘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人欲言又不敢言的事,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一呈上去,却立即石破天惊得到了中央的重视,马上下令取消集体食堂,批转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给全国各地,这真是一份救命的报告,让五亿农民走出饿饭的困境之中。他们为人民立了大功,可也激恼了一些搞极左的人。有人在背后里叫嚷说:‘经济研究所里出了个右派!’” 。
把前面对事实的记述与《孙冶方传》中的描写加以比较,可以说,除了孙冶方高兴以外,《孙冶方传》中的这一段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全都是编造。孙冶方既没有在报告上签署意见,也没有直接呈报中央。毛泽东得到后将其作为弹药收集起来,以备庐山之需。报告并没有立即产生石破天惊的效果,中央也没有把报告批转全国各地,更没有下令取消集体食堂,相反,毛泽东批示以中央决定的方式,指使和督促各地继续大办公共食堂。结果不仅不是救命,反而是进一步害命,不仅没有让五亿农民走出饿饭的困境,反而把几千万人推入饿斃的深渊。不是什么人在背后叫嚷经济所出了个右派,而是毛泽东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公开宣布,科学院昌黎调查组出了个右派。
有人可能以为,作者其所以如此,是为了突显孙冶方的远见卓识和伟大人格。其实,非也。这样做的结果是,给孙冶方的光辉形象涂上了一些异样的色彩。
案例2:在干校批斗会上打顾准的情况与《顾准全传》的描写
经济所的“五七”干校在河南息县,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劳动休息时间,往往要召开批斗会。据说第一次批斗的是秦柳方,批判他在地边撒尿耍流氓,第二次批斗的是顾准,批判他偷奸耍滑。在批斗会上有人动手打了顾准。最早记述此事的是吴敬琏,他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一文中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滑’的‘地头批斗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
由于在干校批斗会上打顾准一事,涉及到董辅礽是否动手,对1982年经济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换届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而影响到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笔者调查访问了当时有可能在场的15、6个人,只有吴敬琏和张卓元确认,当时动手打顾准的有杜某某和杨某某,其他人一概否认或者记不清有这样的事情。张卓元说董辅礽有肢体接触;吴敬琏先对人讲,董辅礽打了顾准,是张纯音反映给孙冶方,张纯音病重住院,对访谈者否认此事;董辅礽也知道吴敬琏这样讲,临终前对前往医院探视他的同事哽咽着说,“吴敬琏到处散布我……”。后来在访谈中吴敬琏对笔者说,董辅礽主持会,没有动手。董辅礽也给孙冶方写信说他没有打顾准,孙冶方看完信说,“看来误会了”。张卓元明确表示:打顾准,我亲眼看到,那天,他身体不舒服,头有点晕。说他不老实,叫他低头他不低头,有人按他的头,他不低头,就打了两下。不是明目张胆地一个拳头接一个拳头地打。张卓元讲述的情况,基本上符合文革中经济所召开批斗会时的一般情形。
然而,高建国在《顾准全传》中写道,“有一次,嗜斗成性的造反派突然心血来潮,把顾准从劳改队劳作的田间,猛地拉了出来,无端地指责他‘偷奸耍滑’,并以此为由,召开‘地头批斗会’,要他认罪服罪。顾准面对刽子手淫威,却无论如何不肯认这个鸟罪。造反派一拥而上,挥起拳头,对带病的顾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打,顾准当即被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造反派得意地问他服不服?顾准忍着浑身剧痛,愤然高喊:‘我不服!’造反派的拳腿像雨点一般又向顾准倾泻而去。顾准被打得惨不忍睹。造反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道:‘你到底服不服?’顾准仍然不肯求饶。他高高地昴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他这一声高喊,换来的当然是更猛烈的打击……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成员,目睹顾准在暴力下,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的这次无畏抗争,无不深感震撼,由衷敬佩。
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以崇敬的口吻说:‘顾准那天在田间,昂起头颅高喊:‘我就是不服!’的情景,至今仍在我眼前出现。顾准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少有的硬汉子!他在黑暗环境中,面对‘四人帮’的淫威,造反派的残暴,真正是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啊!” 。
笔者在访谈中曾经在上海问过顾准六弟陈敏之的夫人,她说,高建国“采取的是写小说的手法”。其实,在文革中,采取各种残暴手段打人、打死人的事例不计其数,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在干校打顾准也是事实,但怎么打,能不能把按头时就手打几下,夸大成雨点般的拳头,一而再、再而三地痛打,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惨不忍睹?当然,打与没打是性质问题,不管是怎么打,凡打人者都是违法犯罪,都是侵犯人权,都在批判或者判刑之列;怎么打是情节问题,是罪过大小的问题,二者有联系,但混淆不得。高建国不是经济所的人员,当时既没有到过经济所的干校,也没有参加过经济所文革中的批斗会,仅凭吴敬琏的访谈和自己的想象,就把在干校打顾准的细节描述得如此绘声绘色,把事情夸大、宣染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采用写小说的手法写传记吗?这不仅不能清算文革的罪行,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案例3:几本《吴敬琏传》中有关吴敬琏的描写
大家知道,吴敬琏是一个著名学者和成功人士,聪明能干,才思敏捷,长于辩论,记忆超群,著述颇丰,成绩裴然,特别是在坚持反对通货膨胀和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吴敬琏的弱点也很明显,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有不少失误,对于一个成功人士来说,有些甚至是致命性的。如,“六四”后给中央写信告赵紫阳的黑状,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赵紫阳 ,借宣传顾准抬高自己,在柳红诉吴晓波抄袭剽窃一案中为吴晓波背书和干预司法等(具体参见《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第016、029章)。
然而,三本《吴敬琏传》的作者都对传主采取了仰视的态度,且基本上都是根据对传主的访谈来撰写的。柳红从1998-2007年做了吴敬琏9年的助手,经过与吴的日常接触和无数次谈话,又找了20多人进行访谈,撰写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家评传—吴敬琏》。吴晓波对吴敬琏“前后进行了6次,每次3个多小时”的访谈,花2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肖像――吴敬琏》。《吴敬琏风雨八十年》是朱敏“源于年轻一代对吴敬琏等老一辈经济学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崇敬心情”,也访谈了江平、张卓元、吴晓求等,与吴晓波的书同时出版。如果说开始时有点过分美誉,那么,其后的描写一个比一个离谱。
在《吴敬琏评传》的“引子”中,柳红写道,“到了70岁这一年,吴敬琏的精神愈加升华,他在不断地超越作为经济学家的思想和行为,向更加博大而精深的思想家飞跃” 。
吴晓波在《吴敬琏传》的开篇“缘起”的标题是,“这个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 。
朱敏在《吴敬琏风雨八十年》的封面上说,吴敬琏“是一个纯粹的人、特立独行的智者” 。
至于这些书中夸大、歪曲,与事实不符之处,不在少数。很多硬伤令人泣笑皆非。这里主要从最后一本书中举几个例子,可见一斑。其中,也涉及到另外两本书。
第59-60页写道,“吴敬琏也参加了该书第一稿的编写工作,并在1961年3-5月,被召集到香山饭店,参加了书稿的研讨工作”。为了佐证,作者选登了一张编写组的照片 ,并在说明中写道,“经济所在香山就《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座谈(前排左一为孙冶方,后排左五为吴敬琏)”。其实,吴敬琏当时参加了于光远《政治经济学》编写组,没有参加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编写组。所以,照片中也就不可能有吴敬琏。后排左五是董辅礽,不是吴敬琏 。
现将香山讨论会合影附在下面:

第83页,“在劳改队,自然而然地,吴敬琏与骆耕漠、杨坚白、顾准、林里夫、张曙光、张守义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反革命分子’待到了一起”。要知道,干校没有专门的劳改队,所有人都在劳动改造。这些人原来都是二排的,但也没有都待到了一起。为了防止所谓“反革命串连”,张曙光被调到四排养猪场。张守一误写成“张守义”。这段话是从柳红《吴敬琏评传》第115页抄来的,所以连错误也照抄不误。
第84页,“此时(指在干校),常挨批斗的吴敬琏,也开始被带到各连去‘游斗’,一天下来竟要被斗好几回”。这也是莫须有的事情。当时,清查的方式是,召开会议揭发批判516,造成压力和气氛,然后由工军宣队和专案组找清查对象谈话,要其交待问题。吴敬琏被作为516的清查对象,不点名的批判有,交待问题的谈话不少,但是,批斗、游斗的事没有。吴晓波《吴敬琏传》第47页也有相同的内容。
第145、146页,作者写道,“1992年3月,在邓小平上海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由周瑞金主持撰写)”。“而此时,吴敬琏也开始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在1991年6月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这里的两个时间都是错误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是1991年3月2日发表的,传达了1991年1月28-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期间讲话的精神。1992年3月已经是南巡讲话以后了。《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是1991年8月份写的,发表在1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上。6月份文章还没有写,就已经发表了。荒唐!
第141页与第207是同一张照片。第141页的说明是,“经济学家张卓元是吴敬琏的好友。图为他与本书作者对话”。第207页的说明是,“法学泰斗江平和吴敬琏创办了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图为他与本书作者对话”。不认识这两个人的人,看了这本书,就会如堕五里云中,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张卓元、哪个是江平?其实,141页错了,207页是对的。
看了以上三个案例,我想,人人明白,不用笔者再啰嗦什么。人物传记居然写成这个样子,足见我们的学品学风已经败坏到何种程度!大家还能容忍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吗?诸位有良知的学者先生们,怎么办?
参考文献:
1. 张曙光,2016、2017、2018,《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经济研究所60年》,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2. 沃尔特·艾萨克森,2011,《史蒂夫·乔布斯传》,上海财经大学出版公司。
3. 李锐,1994,《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4. 邓加荣,1998,《孙冶方传》,山西经济出版社。
5. 陈敏之、丁东编,1997,《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
6. 高建国,2000,《顾准全传—拆下肋骨当火把》,上海文艺出版社。
7. 刘国光,2006,《刘国光文集》(第5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柳红,2002,《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 吴晓波,2010,《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
10.朱敏,2010,《吴敬琏风雨八十年》,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
11.程中原,2007,《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