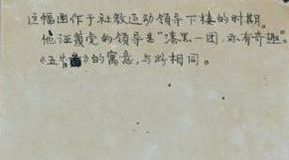【编者按】他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沉静、最隐微、也最不幸的身影之一。曾缄(1902–1968),字仲谋,号寸铁、寸铁堪,四川成都人。近现代学者、诗人、书画收藏家,曾任国民政府西康省厅级职务,1947年辞官后应聘至四川大学任教二十余年。其学问深湛,长于诗词,尤精杜甫、苏轼之学;遗稿所存有《寸铁堪诗稿》《康行集》《折腰集》等,兼有大量关于古籍、佛学、金石、书画的札记与题跋,惜多毁于文革之乱。许多人都对他翻译的仓央嘉措情诗“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留有印象。
作为一位兼具诗人气骨与佛者心性的文化人,他的命运被深深嵌入20世纪中国政治激荡的风暴之中。1960年代“四清”与“文革”期间,因诗词遭定为“反动”,惨遭批斗,晚年悲惨离世,遗体去向多年无从查证。其遭遇,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断裂,更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本文由其后人与幸存者之口述、笔记、访谈、家信及诗文遗存汇整而成。
1947年七月,外公曾缄辞去西康省所任职务,八月入四川大学开始他的教书生涯。
1947年—1968年,二十余年,曾缄先生亲历了国家的多次变革运动,相对平安。到了1965年“四清”,他的厄运来了,而且是灭顶之灾。
我有几则寻访日记,或许可以概述一下当时的情形。
2014年3月11日
今日拜见了四川大学张志烈老师。
可巧,他是“曾缄反动诗选”批判的参与者,那时他和项楚是中文系的研究生。他说别人笑他们说,别的东西没研究,倒把曾缄研究了。他和项楚做一些书记笔录的工作。批判曾缄时,放一把藤椅在中间,曾先生坐中间,批判他的人围半个圈,有些情景还记得:
1) 那份记有“绝密”二字的小册子,是他亲自校对和跑印刷的。当时在“四川文学”印刷厂印刷,有解放军站岗,非常保密,共印250册。曾缄先生事先不知道“川大”将他的诗选出三十五首,供批判用。当时在会场看见发这个册子,张志烈也发给他一本,他看着册子,笑眯了。
(作者注:其实,“曾缄反动诗选”的最初版本是60首,也曾印刷成册,印了多少册,不详。后来又从中筛选35首出来,那个版本,张志烈老师都不知道。)
2) 当时张志烈老师也和别人一样,要针对某些诗进行批判。其中谈道一句,好像是《双雷引》的句子吧,张志烈老师说,你怎么能拿杜甫的诗句这样写呢,曾先生笑笑说:“杜甫的诗里没有这句哈。”
3) 杨明照是专案组组长,他和曾缄先生因为一首诗有点“那个”吧,扬杨说:“曾缄,我们之间虽然有点个人恩怨,但我不会因为这个故意整你,我不是这样的人。”曾先生笑着说:“当然,当然,我晓得你不会的。”传说中因为那首诗,杨明照想方设法要整他这点,张老师说,可能性不大。因为那时的杨明照,虽然在学术上远不及曾缄先生,但他那时是党员教授,很红,没有必要在整曾先生上去获得什么。况且,曾缄先生被整后,66年“文革”,杨明照也被“整”了。
4) 张老师有个话题说“不足为外人道”,就是关于李奇梁和陶道恕。“四清”运动前期,曾先生都没有事,到了后期,曾先生的一首《琼华岛感事》传出来,引起上面的注意,于是开始调查,李当时为曾先生抄写诗稿,然后告发了他。再就是陶道恕,他也抄曾缄诗稿,后来也交出曾缄的诗。张老师讲,“反右”时,李奇良就做过这样的事情。
5) 张老师讲,曾先生是个非常机智和幽默的人,因为信佛,对人很宽容。他讲了两个段子:
其一,60年代初,刘文辉回川,请他以前的幕僚们吃饭,曾先生也在。刘文辉说:“曾缄,57年“反右”,你是咋个滑脱的?”曾先生说:“只许你滑脱,不许我滑脱嗦。”
其二, 新中国建立后,修了一条铁路,曾缄先生有句诗,大意是千里一条铁,庞石帚先生笑他,你看毛主席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多好。曾先生说:“毛主席都写了,我还能写啊?
6)张老师还记得那次展览性批判,在“川大”一个较大的会议室,除了曾缄先生的手稿,还有他的一些书画文物藏品。有一个“寸铁”系着红绳。(作者注:此物曾缄先生在康定时一位活佛所赐,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法物,类似金刚如意。他用红绳拴在身上,自称“寸铁”,后称寸铁翁,寸铁老人。他的斋名“寸铁堪”)。
还有一尊印度欢喜佛铜像,一尺高左右,批判说,这是曾缄收藏的淫秽物品,还有他的山水画。张老师记得“一团漆黑亦有奇趣”的牛图。还有那幅“书空怪事知多少,都在峨眉最高层”等。
废纸卖了。那些被收走的文物,张老师没有提到。
7)关于曾缄先生离世,他讲,“文革”时,他不在系上,家住成都二十八中。他是在曾缄先生去世第二天才知道的,传言是曾缄先生跌了一跤,就走了。开会时,军宣队代表(他不记得他的名字,但还记得他的神情)说:“曾缄是畏罪自杀!”张老师不知道曾缄家属没有见到骨灰。
8) 那场批判后,曾缄先生的文稿,被困成三捆,张志烈老师手书“曾缄反动资料”,放在中文系办公室书柜顶上,后来不见了,据说当成
9) 张老师说,他曾经将《双雷引》交给裴铁侠的儿子裴斐,裴斐根据《双雷引》写了一部小说。(作者注:裴斐是北大的教授,“右派”平反后,他不愿回北大,去了中央民族学院,已去世多年。)
10) 张志烈老师说,尹正良和刘安聪当时都是革委会副主任,尹正良已经去世了。批判曾缄时,当时省长杜心源参加,他说:“曾缄你不要不说话,你这种人,我见多了。”曾缄说:“是,你说的是。”然后还是不说话。散会后,杜对同事说,这个人,真有学识,不简单。
......
我的大表哥张长伟讲,曾缄诗词被绝密批判时,杨明照弄不懂诗歌的典故,更不知其意义,就来找曾缄,曾缄先生就讲给他听,结果他们就用曾缄的话,批判曾缄。
杨明照所说的与曾缄先生的“过节”,就是坊间传说的那首写杨明照的诗。曾缄先生有《读书有感二首》其一:“天然清水出芙蓉,富艳难追谢客踪。笑煞痴儿钻故纸,文心雕尽不成龙”。有说,杨明照把自己的“文心雕龙注”,拿去跟曾缄先生显摆,却不知曾缄先生的先生,国学大师黄侃,早有《文心雕龙札记》问世,被誉为天下“显学”。于是曾缄先生写了这首诗。真相如何,无考。杨明照2003年去世,传说讣告的头衔有近百条,有人在最后加了一句“文心雕尽不成龙。”学校追查了好一阵,无果,不了了之。
外婆赵静仪的回忆录(摘录一)
1964年三月,缄生病住二工医院,不久就出院回家。这时,李奇梁和许存信一批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缄和李奇梁关系比较接近,李每天吃过晚饭就来我家与缄谈天,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才回家去。我觉得他刚刚摘帽子,暗中还有人侦查他的行动,看他和哪些人接触。因为我搞群众工作多年,这些名堂我是知道的。况且中文系有几人就住我家楼上楼下,如李昌,向熹、曹廉,这些都是中文系的人。我就劝缄少和李奇梁接近,少和他打交道,免得别人对你猜疑,缄不但不听,反而大发脾气说我干涉他的自由。我就不管他的事,他实在不听劝说,忠言逆耳,只好由他去吧。五月的第五届选举,我又连选连任,这是我第四次被选为区人民代表,也是我最后的一次。
……
五月的一天,缄学习完了回家,对我说,学习情况变了,他感觉到讨论的发言,有点转移到他身上了。这段时间,我已经发现李奇梁晚上来,有时拿一包纸走,有时又拿一包纸来,他们这些动作都是躲躲藏藏的,不让我看见,都背着我。现在缄感到情况对他不大好,就叫李不要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俩干的什么事。从此,缄显得发愁,也不大进城了。我心里担心他危险,非常着急,但有什么用呢。又想,解放后,经过这么多运动,都把这些难关度过了,也希望他这次能够平安无事的度过这个难关,那就太好了。不幸的是,事与愿违,无可挽回了。从此以后,他每天学习后回家,总说这次是他不易脱身的一次运动,所有发言,都对他是一种暗示。过了几天,我上厕所遇见李奇梁爱人,她说曾老师的问题很严重,因为李和曾老师接近,系上叫他写揭发曾老师的材料。这几天李不能睡,不能吃,看来又要带上帽子了。她说时,很伤心。七月底,楼下住的李淑媛,她是中文系的职员,来家里通知我,说是七点钟叫我去中文系谈话,她和我一道去。我当时一身都冷了,知道是要我揭发缄的问题,但是我根本不了解他的事情。六点半,我和李一道去了系上,是陈志宪、邱俊明接待我的。首先他们问我知不知道缄的事情,我说我只知道他犯了错误,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他们就对我说,近几年来,曾缄写的诗词全是反动的,不但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毛主席。但是他又写得非常隐蔽,没有那种水平是看不出来的。我们也知道你没有看过他写的东西,你不要多心,你就是看了,也不懂他的含义,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水平。现在就要曾师母对他多多启发,帮助他好好地把写这些东西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思想指使他写的,写了要表达什么目的,对社会上要起什么作用。叫他挖出来,挖的越深越好,这就是区别他认罪的态度,否则其后果就由他自己负责 。我们知道你思想比他好,又是几届的人民代表,所以托你帮助他,一定会比别人帮助好。我当时表示愿意开导他,打消顾虑,好好交代,谈话就此结束。回家来,我对缄讲这些话,问他,经过这么多运动,怎么没有一点警惕性,写这些不合时代的诗词,对你有什么好处,这些诗词是怎么透露出去的?开始,他不说话,过了几分钟他才说出诗词放在李奇梁处,托他帮我抄写。那么,事情坏在哪里,也就真相大白,不再介绍这个人。从此,缄每天要去系上学习,听别人批判和自己交待。九月的一天,系上通知他两点到新会议室开批判大会,阵容很大,全市的大专院校中文系教授都请来参加会议,主持人是杜心源,许奇之,并把缄的诗词印成小册子,发给每个人一本。会议结束时,杜心源当场宣布说,李奇梁这个月生活有困难,可以津贴他20元钱。此人良心黑透,出卖一个快八十的老师,也才得到20元奖金。我想,缄的心中可能也有点后悔,但是已经不能挽回。十月,第六届普选,我当然没有资格当选了。于是孙嘉惠丑态百出,极力吹捧张佩松的爱人刘毅为代表。我受缄的影响,人民代表就此结束。十一月,系上又说缄手里还有最宝贵的东西,叫他交出来。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他哪有什么宝贵东西呢?只好把他保存的佛像和他亲笔写的手稿装了一包,叫桂溪提着,陪他一道交去系上(作者注:我姨爹叶桂溪的回忆,东西装了一个三轮车拉过去的。)
关于曾缄先生之死:
版本一:被红卫兵从批斗台推下,眼睛大出血而死;
版本二:抓他的人,楼梯间推搡他,摔死的;
版本三:被踩死的;
版本四:拉去批斗会路上猝死的;
版本五:在“川大”一教学楼集中时死的;
版本六:某军代表讲,大家搞清楚,曾缄是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川大八.二六”参谋长,刘安聪回忆录:
1968年10月23日,市革委要求全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作为造声势的手段,指定当天夜晚统一行动,各单位将本单位的牛鬼蛇神统统抓起来。军工宣队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分头抓人,确定第一教学楼为收容点,指定我负责收容。夜半三更入室拿人,是一件现场尴尬事,事后难堪的嗅事。军人不便为,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不愿为,正与军工宣队顶牛的学生,不屑为,所以由驻校工人充当临时捕快,个别投靠新权利中心的人隐身于后,做做圈名单,开住址,带路引路之类的小勾当。
大约晚上十点钟以后,陆续有工宣队队员将捉拿的教师、干部反剪双手押来报到,由我处收押。进入教室或蹲或坐,个个面色惊惶,不知所措。共数十人,多为有历史问题的老先生。我亲眼看见两个工宣队员押运,另两个工宣队员架着一个又矮又瘦的老教授走来,教授的双腿垂在地上滑行,将人拖进教室放下,工宣队员说,这老头是从被窝里拉出来的。我近前看,老人瘫在地上,一动不动。我单膝跪下,俯身将老人的头置于我的手臂,另一只手摇晃他的身子:“喂,喂,你醒醒,你醒醒!“老人没有反映,安详的躺在我的臂弯里。请校医,快请校医!”几分钟后,校医赶到,宣布老人已经去世。我“下跪”,不是向老人示敬,而是方便检视老人状况。我喊“喂,喂”,不是对老人不敬,而是不知姓名,不知如何称呼,便使用了中国人惯常的呼叫用语。遗体很快被人抬走。我用眼光寻找那几个工宣队员,他们早就溜了。多年来,老人临终的情景,一直在我心中盘旋,隐隐作痛。老先生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死在我怀里的人。人活在世上不容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多一些些关爱,少一些些伤害。接连三天,我便守着这些牛鬼蛇神。我去找工宣队负责人,成都仪器厂革委会副主任,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小伙子。我说死人了,他说死有余辜。我问牛鬼蛇神名单怎么来的,他说不知道。我问这些人有什么问题,他还是说不知道。我问这些人怎么处置,他还是说不知道。此人在军工宣队和校革委联席会上,一向傲慢,联想到“八·二六”冲锋陷阵时,他不过是摇旗呐喊的小伙计,居然给我打官腔,居然不讲政策胡乱来,我冲他说:”“这就是你们搞的的清队?连我们都不如。你们要对死人负责!”小伙子不甘示弱,与我争执起来 ,我把手一挥,“这个看守所长不当了”,拂袖而去。此后一段时间,江海云和同学们调侃我:“刘大官人当弼马温,真是委屈你了。”
2012年,一位朋友告诉我,网上有篇文章讲了川大某教授之死,指责“八·二六”太过残忍,我一听便听出正是这桩事。我讲述了过程,朋友愤愤不平,欲撰文澄清事实,被我劝阻。事情发生在1968年,作者联想到那是造反派猖狂的年份,便断定是“八·二六”所为,系“八·二六”以校革委的名义所为。他却不知,事发时,“八·二六”已经解散,高年级学生已经分配,军工宣队已经将校革委架空,我还就教授的死,与军工宣队发生争执。该文作者的“想当然”产生了张冠李戴的效果,不经意将张三的帽子扣到了李四头上。
2015年11月21日,我收到一条短信:“刘先生,您好,我叫曾倩,是曾缄先生的外孙女。曾缄先生诗集《寸铁堪诗稿》已出版,我想送您一本。非常期待能见先生一面。谨祝冬安!”搜索记忆,我并不认识曾姓祖孙,遂打去电话。原来曾缄就是死于非命的这位老教授,曾倩是那篇博文的作者。电话里,我向她讲诉述了她外祖父亡故的经过,我们都流了泪。也是机缘巧合,21日上午,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倩与我那位朋友见了面,朋友向他转述了从我这里了解的情况,而几十年来,曾倩及其家人,毫不知晓外祖父的遭遇,只是第二天收到川大出具的一份死亡证明。24日,我和曾倩见了面,我将自己的忆文送给她,她将外祖父的诗集签名送我。她早已泣不成声,我听凭她宣泄压抑得太久太久的冤屈,我从心底缅怀逝去的老人,从心底祭奠许许多多无辜的死难者。
外婆赵静仪的回忆录(摘录二)
十月24日即农历九月初三,早上七点钟,我起床不久,就有三个小伙子到我家来,大声叫喊曾缄去大操场开会。我说,曾缄病得走不得。他们说,没有你说话的份。他们去到里面,看见曾缄睡在床上,就叫他快点起来,马上就走。缄起床,穿起衣服坐在马桶上小解,嘴里哼哼唧唧,他们就叫他少装点疯,快点走。缄说:“我病了嘛。”他们又催:“快点走!”就这样,缄和家里的亲人就永别了。缄走后我仍然搞我的工作,十点开始煮饭,十二点还没有回来,我和小英就先吃饭,菜放锅里蒸起。碗筷摆在桌上,准备他一回家就吃饭。一直等到两点钟,都没有影响,这时我感到事情危险,可能是把他弄去游街了。到了三点钟,系上来了三个人,二男一女,女的我认得,姓廖,在十四宿舍住过。她气势汹汹的高喊,曾缄为什么不到系上去?我说,曾缄没有回家来。她训我不老实。我气急了,大声对她说:“我还在等他吃饭,碗筷还在桌上,你们请到屋里来了解。”她说是不是躲到城里去了?我说他是一个病人,绝不会这样做。两个男的看她这样凶,就对她说,我们没有散会就走了,不了解情况,现在还是到系上去看看就知道了。这个泼妇才没有再说什么,三人一道走了。时间快要四点了,我想就是游街也该回来了,莫非他已被捕了?也要通知家属给他送被盖去。究竟怎么回事,真把人急死了。这时叶桂溪来了,说是街上惨得很,到处都在捕人。因为令慧满月,他去医院拿药,听樊成炳说,今天川大工宣队有一人生病了,去医院看病,谈起早上川大开批斗会的情况,说是会还没有开始,就死去了一个瞎子老头,他不知道姓名。樊成炳说,可能是曾令慧的父亲吧?川大的详细情况现在还不知道。我说,伯伯的这种情况早在我意料之中,因为他的癌症已到了晚期,又没营养,又在床上睡了一年多,突然叫他去开会,当然心里又紧张又吓又怕,又走那么远,有可能发生不幸的事。现在听了这个消息,我要好好控制自己,不要悲伤过度,才能办理他死后的事情。叶桂溪走后,五点过,我带小英出去走走,目的是想听川大的消息。一出大门,就碰见孙嘉惠皮笑肉不笑的一脸扯相,问我曾老师回家没有,她们缝纫组有人看见抓起走了,又有人说病倒了,学校通知你没有?我看她那个样子,心里很气,但是我仍然做得很镇静,对她没说什么就走了。到九眼桥去走了一转,也没听见什么,只好回家来等候消息。一夜过去了,次日吃过午饭,还是石沉大海,消息全无。从此,我一出去,群众就追着看我,悄悄地议论,我心里难过极了,对着群众的哭脸,还要装成笑脸,这样的日子,真令人无法忍受,不忍受又有什么办法呢?午后六点钟,悄悄地去与文里找李婆婆打听消息,据她说,她的爱人李景清,开会的头天晚上半夜三点钟,就被抓去开会,当天午后了,六点钟广播上喊话,叫牛鬼蛇神的家属,送被盖衣服到牛棚去。她送东西没有看到亲人,是由红卫兵接去的,其他消息一点不知道。三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川大也没人来家里通知我。但是人死了,就该去办下户口和粮食退票证,这是政策,如不去办,又要犯错误。缄死的消息没有落实,我又凭什么呢?考虑几天才想出一个办法,只有等到十一月十号发工资那天,我仍然去领生活费,就能把这件事落实到。到了十号早上,我心里非常紧张,还是鼓起勇气,到财务科去,发生活费的人是认得我的,他对我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我就把缄的私章交了进去,他马上给我扔出来说,人已经死了,你还来领生活费。我当时问他,曾缄死了我怎么不知道,学校为什么不通知我?他说没有通知你吗,我们是得了通知的。这就把死的消息证实了。我由财务科出来就到川大保卫科,请他们勾销缄的名字,因为牛鬼蛇神的名字由保卫科登记下来,什么事情都要去报告科里。负责人黄荣历来就认识我的,平时对我很尊敬。他见我去了,马上让我坐,还给我倒了开水。停了一下,我才把这件事情对他谈了,并请他将缄的名字撤销。他听了我的话,很吃惊,说是曾老师死了?他们都不晓得,学校也未通知他们。我看他把名字注销了,就回家来。在路上遇着许多职工家属向我了解情况,我只好敷衍几句,有的人表示难过;有的人对我安慰;有的人没有表情。回到家里,虽然伤心,但为了还有多少事情要我办,只好自己劝自己。次日,令筠和令慧俩姐妹去川大办清公室,请问他们缄的错误究竟是什么性质?现在缄死了,要他们出具证明,我们要去派出所下户口。结果他们写了一张五类分子的证明。令筠她们又问,缄的遗体在哪里?他们说,早已火化了。两姐妹又叫他们把火化的卡片交我们,他们说没看见什么卡片,更不知道遗体火化了,还应该有什么卡片。午后三点钟,我去派出所,是时,这些机关已经军管了,由解放军办理户口的事。她问这个人具体属于哪一类,我说不知道,清办公室没有说明是哪一类,只给了我们这张证明,他说,川大这些人,办事怎么这样随便……
缄死后的一切,按政策规定办完了,遗憾的是缄的遗体火化了,他的骨灰和火化的卡片,今年十四年了还没有着落,总觉得对不起缄。但当时那种混乱,所有的亲人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彻底明白,是办不到的。缄死而有知,也会对他所有的亲人原谅的。缄逝世后,我心里很悲伤,我给他写了挽联:
四十年长期相处,人世荣枯与君同受,
数小时仙凡永别,地下狐狸为我先驱。
缄去世今年十四年了,我和他结婚整整四十年。现在我把对他四十年的看法写个总结评论。他是一个好人,有道德,有修养,他是才子,文学家、诗词家。他学问渊博,目空一切。只专学问,不会处事。他看得起的朋友,就不管其人的好坏,他对朋友真诚坦白,朋友就是欺哄他,他都不会感觉到,以至对李奇梁认贼作父,把自己弄成那样的下场……
外婆的回忆录,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写完的。
世姐杨橘荪说,听闻曾缄先生走了,她的爷爷,曾缄先生的好友杨啸谷先生恸哭:“慎言不慎,奇梁不良。”
曾缄先生就这么“走了”,他不仅是位诗人,还是学者,他的杜甫诗歌研究,东坡诗歌研究和一些学术论文,体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惜,他的杜甫诗歌研究文稿,只有片语了。东坡研究,从遗留下的手稿看,也没能完成。他还是佛者,笃信佛教,听我母亲讲,家里有佛堂,供桌供一排十二樽鎏金金佛,十二盏长明灯,没有熄过。他还是收藏家,字画,名砚,玉器等不少。家里有一隅,全都是他的砚,阿婆称为“石头城”。外婆曾经埋怨他,把钱都拿去卖古董,我妈和我三姨妈开学了,竟然交不起学费。三姨妈说,解放后,家里收藏的文物,三分之二捐给了西南博物馆,家里留下的东西,他被批判时没收,文革又抄家,没有了。家里有史可法对联,东坡手卷,宋朝百马图,刘宋永光年白金造像佛,巨鹿出土的古秘色窑印盒,金花眉子歙石砚,元武珍哥铁砚等。这方珍哥铁砚,曾在2009年5月8日四川文物总店展销时,出现过。有一年春节,曾缄先生为自己的古董盘存,为他的十一件宝贝,写了十一首诗,其中就有一鼎商觚。三姨妈讲,那时外公说,卖了这个觚,全家周游世界两圈,都用不完。
退休后,我致力外祖父的诗文收集整理,历时七年,终于出版了他的诗文集《康行集》三卷(《寸铁堪诗稿》《康行集》《折腰集》),个种感慨,感慨万千;个中滋味,别有滋味。时不时我会与外公的“神交”。
2012年5月10日 晴,周四。
希望穿越时空,与外公曾缄先生对话,用灵魂和血肉。
我的每一滴血,每一个细胞,每一个DNA都“痛”,这种痛,无可言说。
2012年四月九日晚间上网,我意外与他相遇,这个我一生中,只和他一起呆过一个星期的人,那时我才两岁。他对我的“撞击”,如霹雳一般炸在胸间,我踉跄后退,背贴冰冷残酷的历史之墙,几乎窒息,直到心灵恸哭,涕泗滂沱。
我是他生命因子的延续,是他社会关系中的一段血脉。他于我,是前不见的“古人”,那么渺远,仿佛不在一个星球。他早就走了,我十岁的时候。1968年10月24日,那天黑云压城,风雨如晦。他走了,坊间有N个版本流传,他的走法,每一个都会“痛”死人。但是,他去了哪里,究竟怎么“去”的,去得痛苦还是安详?他的遗体被尊重吗?他的遗体是火化了吗?谁签字火化的?他的骨灰呢,存放在哪里?半个世纪过去了,阿公啊,你可瞑目?阿公,托梦给我,让我找到您.....
2014年元月8日 22:44
前日,江功举先生来电话说,找到三本外公的书,让我去拿。今日上午,我到了他的“浣花雅集”,江先生将《归田录》,《老学庵笔记》,《孝经正义》送给了我,我非常意外,非常感激。三本书,都有外公的点注。
傍晚七点左右,江先生来电说,今日是“腊八”,他也是与人吃饭,才知道今天是“腊八”。我心里一惊:“今天有本书提了‘腊八’的!”江先生说:“这事情有点巧”,我也讲:“是啊,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啊?”“你记一记吧,这事很有寓意。”放下电话,我拿出那本《孝经正义》,书本最后有外公批注:
壬辰岁腊八,是先慈生辰,适得明版孝经一册,此吾家经也。冥冥中有吕招我也矣。予七岁失恃,今寿满六十,显扬之效盖无闻焉。捧读再四,不知涕之涟洏。曾缄谨记
“腊八”是曾祖母的生辰:1952年“腊八”,外公得此书,今年是外公120年诞辰。也就是说,60年后,这本曾家经,又回到了曾家,到了我手里。这60年,这本书有何辗转的经历?此书封底封面皆非原装,书中诸多被虫噬的痕迹也被精心修补过,这是何人所为呢?为什么在今年的“腊八”,它又回归了呢?冥冥中,上苍有所昭示吧?腊八 ,腊八,腊八。三个腊八,三个巧合,一脉相承的至亲,灵犀相通,穿越时间的隧道,外公与他的慈母相见,我与外公相见,相隔都是六十年,一百二十年,我们隔了四代,却在同一天相见,真是人间奇事......
这些多年来,我把自己埋在故纸堆“穿越”,前世的各色人等,纷至沓来:有的目光如炬,有的噤若寒蝉;有的光明正大,有的卑躬屈膝;有的不卑不亢,有的形骸猥琐......我对人性的认识,本来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的范畴,却不道,真善与伪善,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一片混沌,泾渭莫辨。历史更替,政权易帜,社会变革中的各种运动,纷至沓来,撕裂、整合着一个新的时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异常激烈,他们能保全自己健全的人格,把控自己的命运?不能。这是他们的宿命。曾缄先生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这样的悲剧,万不可重来!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